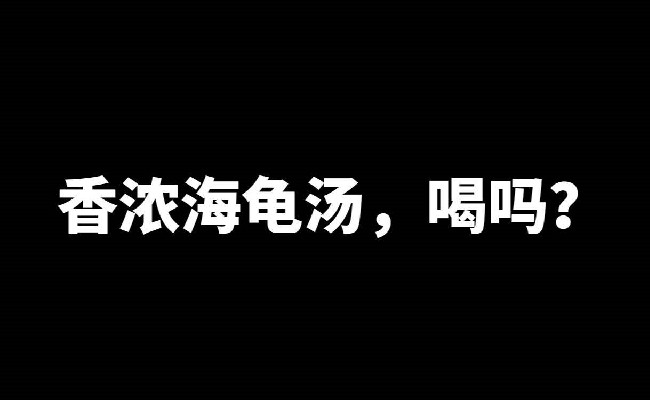制造谜语再揭开谜底,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趣呢?
(借助《作文素材2018年第4辑(下)》侦探小众专题导读与运用完成此篇)
正如阿瑟·柯南·道尔对《福尔摩斯》中故事的定位隐藏树叶,在森林里;隐藏尸体,在战争里;隐藏都市传奇,在日常生活里那样,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一蔬一饭,阳光雨露,家人的关心,邻居亲切的问候都无法掩饰生活背面的阴暗和潮湿。而发生在熟悉城市生活中的推理故事,正是这乏味生活的一剂解药。在侦探眼里,屋顶的颜色,行人的衣着,橱窗里的陈设,城市的每一砖每一瓦甚至连路边无端倾倒的一颗樱花树,都可能隐藏着破案密码。在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制造谜语再揭开谜底,还有什么比这更有魅力呢?
侦探是现代人留给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自我书写和打造的都市传奇,他在文字里诞生,在城市的钢筋铁骨里成长,与雨水和雾气融为一体,最后尘埃落定,还原为我们的邻居,朋友和亲人。
作者是躲在侦探背后的影子。第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一生命途多舛,身边亲人多遭不幸,其笔下的侦探杜宾也不近人情,更像是一部冷血的推理机器;曾学医的奥斯汀·弗里曼,无论是他笔下极具崇尚物证推理的桑戴克博士,还是他开创的反叙述性侦探小说,都体现着实验精神所在;阿婆阿加莎由于女性特质,笔下的名侦探都善于推敲人心,进行逻辑推理,找出真凶。没有作者,侦探也就不复存在,侦探同样投射着作者的特质。
侦探最有魅力的一刻,当然是破案之时。每一个侦探都有最经典的案件推理,那于揭露罪恶绽放中的智慧之花,是我们迷恋侦探的理由之一。密室杀人模式中密室的密封程度和空间大小使其成为不可能犯罪的代表;安乐椅探案不能进入犯罪现场,不参与证据搜集,更多利用报纸、不同人不同视角的证词、对不同人的察言观色去揭开谜底;破译密码既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流露和对读者智力的挑战,又是读者窥探作者思维奥秘的途径;不可能真凶模式最大的魅力在于结局的反转,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发出凶手竟然是他的感叹;心理盲区是潜意识里被遗忘的角落;而暴风雪山庄模式最大的看点就是幸存者之间慢慢产生猜忌和怀疑,信任逐渐被打破,人性崩塌的过程。罪案谜底与其说是犯罪者与侦探的斗智斗勇,不如说是侦探借之向读者展现魅力的高光时刻。
大诗人泰戈尔写过绿叶颂,而侦探助手就充当着不引人注意的绿叶,虽然他们的存在感很低,但确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嫌疑人X现身》最后,局外人帝都大学教授汤川学的介入,让警察解开了主人公数学天才石神哲哉设的迷局。然而,与其说石神被汤川学揭穿,不如说石神利用了汤川学,他想要找到一个人帮他在警察面前把案件推演得更确凿一些,也需要一个人,哪怕是敌手,能够懂得他的一片真心。而知道真相的汤川学也并不会做出有违逻辑之事。处在逻辑之中的两位高人,彼此钳制,却又彼此理解,侦探与罪犯,却成为潜在的互助者。石神为了爱情而犯罪,令人想恨又恨不起来,看似帮助靖子逃脱牢狱之灾,但靖子在知道了真相后却选择了自首,前夫的生命,乞丐的生命,靖子的生活,石神的生活,在石神的苦心计算下,却无一受益,悉数坍塌,这或许就是罪犯的宿命。而找到真相的侦探也对此唏嘘不已,留给读者的,是无关是非黑白的人性地图中的灰色地带。读罢只觉无尽怅然,彷如独立荒原。没有助手,侦探的智慧难以得到衬托;没有助手,读者的疑惑难以借此抛出。他们是侦探的同伴,同样也是守护着这份指挥部滑向罪恶深渊的守护者。
侦探小说的第一本质在于,它是最初且唯一可以表现城市诗歌气质的大众文学。
侦探小说无疑是现代都市生活和印刷资本主义合谋的产物。城市工业文明的取代和激烈的社会变革使19世纪的英国和整个欧洲蹒跚前行,肆虐的瘟疫和绝望的情绪如幽灵般在城市的贫民屋蔓延,没人知道何时得到救赎。此时,极端者以犯罪为乐,与此对应的当权者无法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以消除产生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借助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来对抗日益增加的城市罪犯,从而使罪犯与反罪犯具有了空前的技术含量,成为一门货真价实的学科。
而同样获益于城市发展的报业资本家们也很快发现罪犯与凶杀的新闻可以带动发行量上升。但能够吊起读者胃口的罪案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而对于需要定期发行才能保证盈利的报纸来说,描写犯罪的连载小说就成了最合适的替代品。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就诞生在这样一个需要都市传说和超级神探的时代。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无论是柯南·道尔或是福尔摩斯都无愧于他们的时代——尽管那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却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视的遗产。
侦探身上所凝聚的对正义的渴求,对复杂关系的辨析,对真相的揭露,是城市居民面对难以理解的城市信息的欲望投射。当侦探解决了迷题,读者也觉得城市变得可以认知和把握。侦探小说向人们提供了解脱危机、焦虑、困境及认识和控制大都市的可能。
一个侦探代表着一所城市。柯南·道尔设计的侦探故事,结构其实很简单,刑侦中交织运用的基本演绎法和化学、物理手段让人目不暇接,直接印证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于科学与工业的依赖迷恋。犯罪与文明在近代城市中如影随形,坏时代与好时代相互冲撞,奔向各自的天堂和地狱。难怪有人会认为,全世界的人都需要回忆黄金时代的福尔摩斯,如同中国人需要向往盛唐,这种情感无法复制。
侦探小说在美国诞生,同样在美国颠覆。肇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工人失业,人民贫困,官吏贪污腐化,社会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美国诞生了硬汉派侦探小说,在这类小说里,侦探不再是无所不能的天才,他们也常常落入尴尬的处境,游走在违法或破产的边缘。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便是硬汉派的代表。他或许是最失败的名侦探,他会因调查取证失败被警察暴打,关键时刻还要漂亮的客户秘书帮忙......他醺酒,孤独,疲惫,躲在脏兮兮的事务所里,在劣质香烟的烟雾里阅读案件材料。钱德勒的特质在于,用极富镜头感的语言构筑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浮世绘:被酒精和香烟缭绕的城市街头的霓虹和小酒馆,商业大楼里埋藏的人性阴影。
如今,夏洛特·福尔摩斯的维多利亚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今天刑侦科学的发展也让演绎法显得不那么神乎其技。无所不能的名侦探总有一天会老去,就像今天,侦探小说早已不是小说的主流。那么我们为何还会迷恋侦探?
事实上,侦探,或者说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蕴含着从我们内心深处想要得到的东西——了解世界,掌握世界,得到真相,履行正义的愿望。因此福尔摩斯是不朽的,只要这个世上还有扑朔迷离的悬案,福尔摩斯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名侦探。